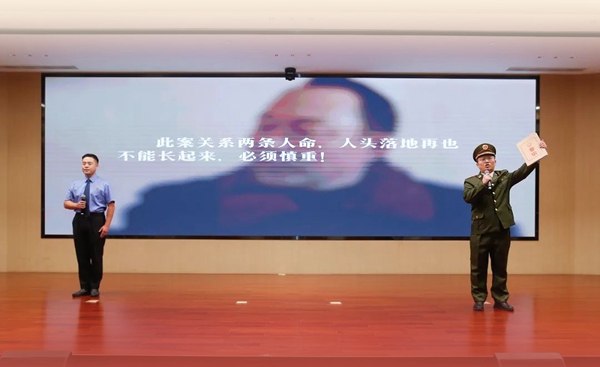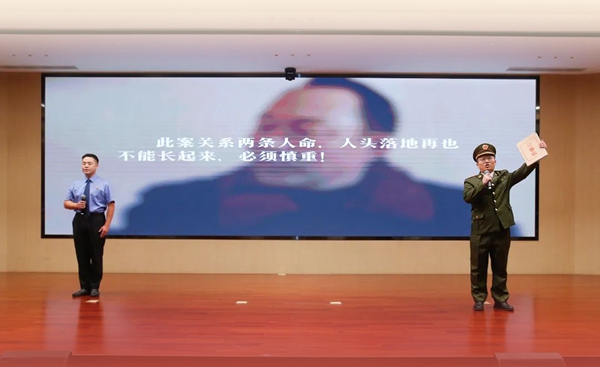根据“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针对案件具体情况,探索证据开示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和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及自愿性。据此,有的地方检察机关开展了相应探索。如江苏省如皋市检察院制定出台《如皋市人民检察院认罪认罚案件证据开示工作规定(试行)》,明确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被追诉人拒不认罪或对部分事实有异议的,检察机关经评估认为通过证据开示可能促成其认罪认罚的,可以进行证据开示,并探索形成《证据开示清单》,全面出示与定罪量刑有关的证据,开示活动全程制作笔录并同步录音录像。山东省邹平市检察院出台《邹平市人民检察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证据开示工作手册(试行)》,规定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检察机关决定进行证据开示的,制作证据开示清单和量刑计算表,在检察机关举行的证据开示会议上将上述材料交由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阅读,针对问题进行解释,等等。
一些地方检察机关结合认罪认罚案件对证据开示进行有益尝试,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良好成效。如,将证据开示与加强释法说理有机结合,邀请值班律师一起参加,等等。但是,也应看到,认罪认罚案件证据开示的范围、时间如何把握,实践中也存在不同认识。笔者认为,深入探索认罪认罚案件证据开示,应准确把握证据开示制度与阅卷制度、公正与效率、打击与保护三对关系。
一是准确把握证据开示制度与阅卷制度之间的关系。在刑事诉讼中,由于控辩双方可以动用的诉讼资源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建立一种制度来保障被追诉人对公共司法资源的使用。基于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不同,存在两种不同进路:前者为“案卷移送主义”下的阅卷制度,后者为“起诉书一本主义”下的证据开示制度。我国主要采取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传统刑事诉讼中采用的主要是一种保障被追诉人一方阅卷权的方式。现在探索的证据开示,主要还是基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知情权和认罪认罚真实性及自愿性目的,检察机关对相关证据的开示,也是在现有阅卷制度的大框架之下进行的,且证据开示与阅卷制度在功能上具有一定的重合性。由此可以推导出,证据开示制度相较于阅卷制度具有功能上的“补位性”。具言之,虽然从理论上能够推导出证据开示制度可能适用于所有案件、任何被追诉人,但基于证据开示制度主要是为了弥补控辩之间的“信息不对等”,尤其是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阅卷动力不足而导致的仅仅是“有帮助”而非“有效帮助”等问题而来。所以,在当前的实践探索中,要深刻认识现阶段证据开示相对于阅卷制度的补位性质,以防试点探索中出现发力错位。
二是准确把握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永恒而鲜明的主题,二者之间的张力在“程序从简”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更为凸显,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的进一步完善,抑或是对于相关配套机制的建立健全均不无助益。公正是首先必须坚守的价值追求。对此,可以规定检察机关根据被追诉人是否处于被羁押状态,具体确定证据开示时间。如此,不仅可以为辩方的证据评估提供相对充分的时间与空间,而且还可能使得办案机关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被追诉人少捕慎押,进而达到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目的。与之相关的还有在探索中形成的所谓“证据开示清单”或“量刑计算表”开示模式,此举聚焦被追诉人最为关心的量刑问题,同时展示相关证据内容,既精简又抓住了核心焦点,能够切实保证办案质量,促进司法公正。
而且,从实践探索来看,证据开示的范围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效率的价值追求难以回避,而全面开示证据所带来的程序负担加重、干预控方证人的风险提升,以及由此引发的诉讼效率降低等问题亦与制度初衷相抵牾,不得不予以考虑。由此出发,笔者认为,证据开示应以可能对裁判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主要证据为限,重点开示可能导致被追诉人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证据,尤其是实践中经常会从中发现存有对被追诉人有利情形的证人、被害人等前后不一致的陈述、不具有证据能力或已被排除的非法证据、讯问录音录像资料等。
三是准确把握打击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刑诉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提升了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由此出发,在证据开示的启动上,除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以外,应进一步提升被追诉人一方的申请权重,如若证据开示申请不被允许,检察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为了更好地兼顾打击与保护之间的关系,也应适当探索双向开示,在承认控方开示存有例外,如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开示后可能影响侦查、有碍抓捕等证据不予开示情形的同时,强调在证据开示这一控辩对抗“调节器”上控方负主要的开示义务,而辩方仅在刑诉法明确规定的三种情形下承担开示义务。此外,对于不开示证据的后果,从制度初衷出发,不应单纯通过理论推演简单以程序性制裁的形式予以否定,而应构建强制证据开示程序,以实现打击与保护的兼顾。